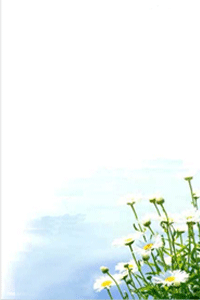当前位置:社交恐惧症首页 >>
人际关系障碍 >>
当前位置:社交恐惧症首页 >>
人际关系障碍 >> - 人际关系心理障碍的儿童期经历原因 (9)
- 心理邮箱362890071@qq.com 转载请注明华人心理咨询网www.hrxlw.com
- 华人心语心理咨询电话02784530206 网络网上在线心理咨询QQ:362890071
- 许且可以忍受的。在充分抱持的环境中,婴儿能够自由地以本身存在的状态发展;婴儿并不总是必须有反应。在最佳的抱持状态中,自体进入存在,而不受外部侵入的影响。
当抱持不充分的时候,就会出现温尼科特(1975)所称的“冲击”的危险。如果刺激的强度超过了婴儿自我功能能够承受的程度,会导致创伤性伤害,从而导致个体使用分离性防御。不仅自我的发展被中断,而且正在成长的个体会变得害怕外界世界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婴儿的能量必须被引导到阻止外界侵入的方向上(很像当外界巨大噪声干扰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反应)。
在生命稍后期,好的抱持环境也类似地提供了容器的作用。在这个容器当中,人们可以探索他们自己的能力,而不受外界需求和喧闹的影响。例如,一个好教师会给予学生探索、犯错和不知道的权利。相似的,治疗师也学会很高兴地接纳治疗当中出现的静谧空档,让患者在这个时刻作为自体而存在。
第二部分 第3章 抱持(4)
人们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往往是当他们情感上正在成长的时候,他们需要感到被抱持。他们需要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他们能体验他们自身令人恐惧或躲避的部分。他们需要知道这个结构不会“令他们失望”。他们也需要相信,他们不会被那些不受欢迎的建议或治疗师的冲突或困境所侵犯。临床医师努力对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这使得心理治疗成为对抱持环境的一个最好的理解。当病人面对他们的记忆和情感生活中那些无法独立面对的令人非常恐惧的方面时,治疗师会“抱持”病人。(我的一个病人曾这样描述她的治疗经历:我坐在她的旁边,而她正面对内心的恶魔。)即使病人因对治疗师感到失望而对治疗师发怒、与治疗师竞争、嫉妒治疗师或对治疗师大喊大叫时,治疗师仍继续抱持病人。即便关系带来痛苦,充分的抱持仍继续进行。
好朋友彼此之间也会有刺激。我们经常彼此向对方“卸下”一些强度过大而无法承受的情感,只希望另外一个人和我们一起承受,而不是让他们破坏这些情感。通常情感支持便是这样一种包容的形式,吸收了过度刺激的部分,将它变得不那么有害。我曾得知一条西班牙俚语,从字面上来翻译是,我能让一个人“成为我的银行”,也就是说,让某人为我保留并保护我的感受,允许我远离这些感受(MarcosLichtmajer,写给作者的信,1990年2月)。
情感支持
在提供支持的时候,人们尽他们所能来保护另一个人不坠落。感到被支持也是感到被照顾,感到一个强有力的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体验。在最早期的生活中,无助婴儿对食物、舒适感和温暖的基本需求主要由抚养者满足。后期,婴儿学习走路的时候,需要握住他人的手。再后来,成长中的儿童学习在日益复杂的社会里行进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建议和指导。被以这种方式充分抱持的体验(既保护又掌舵)与情感和赞许的体验是不同的。
娜塔丽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试图理解她被养育的矛盾方式。“我的母亲很和善也很招人喜欢。我和父母之间有很多身体上的情感表达,很多拥抱和亲吻,我的母亲经常告诉我说我有多棒,说她是多么爱我。但是我知道,我父母中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儿。”在关系图谱上,娜塔丽画了三个姑姑,将她们描述成“给我们提供给养的人。她们带给我们需要的东西,有时候带我出去买冰激凌,后来还帮我们做家庭作业。我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很多爱,但她生活的目的是要改变我的父亲,让他变得有责任心。她从未做到,但她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试图改变他的方面;然后,她变得非常疲惫,筋疲力尽,无法做其他任何事。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你的父母不试图为你改变一些事情,你对他们来说就不是真的重要。我感到我不得不依靠自己来学习。”娜塔丽能感到她母亲对她的感情和赞许,但这些并不是她所需要的抱持。
抱持的支持成分,其原型不仅存在于被满足的儿童的生理需要上,也存在于儿童学走路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引导和牵引。在过渡阶段可以获取这样的支持,在一生当中都是必要的。当我的被试们描述他们的冒险以及危机情况,或当他们的生活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最容易谈论对“支持”的需求。要成为完全的自己,或遵循一条与家庭期望完全不同的生活之路的愿望,必须取得来自他人的大量支持。
例如,马克(Mark)的父母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成为了一名舞蹈者,他依靠与他心意相通的叔叔的支持来承受父母的反对意见。马克回忆起来自父母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嘲笑,他们认为跳舞是娇里娇气而且愚蠢的事情。他痛苦地回忆起被嘲笑和被愚弄的情境。每当在哪种时刻,他就会想起叔叔的支持性话语:人生中重要的事情是成为你原本就是的那种人,盲从他人所思无异于地狱。马克说,每当他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怀疑或不确信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叔叔的这些话而“坚持”下去。
当有一个人信任我们(在我们身后撑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被支持。“支持”一词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抱持”这一隐喻之中。在我们的研究中,人们对支持性事件和关系的记忆能引发深刻的感激之情。有时候,支持成为长期的依恋关系或友谊的基础;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支持性关系只对那些不畏艰难险阻而前进的人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只要他们还需要这种支持。
我们可以看看人们对那些悲伤的人是如何反应的。他们带来烘烤的食物,提供具体的帮助,尽他们所能来帮助—似乎在说,“尽管我无法提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我就在这里,你需要什么尽管从我这里取”(也就是说,死去的那个人)。那些试图安慰丧失亲人的人试图象征性地以戏剧化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作为容器而继续运行着。在支持团体中,人们彼此支持,来填补任何他人可能失去的资源。例如,在AA团体(即匿名戒酒协会)中,“伙伴”就是支持者,他在那里帮助人们克制不去喝酒。当人们对冲动的控制力减弱的时候,就可以“求助于”他。
这种支持的形式是一个错综复杂而且似是而非的过程,因为它从外部提供了做人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的可能性。瓦瑞给埃德打电话,这样埃德就能告诉他不要喝酒,这恰恰是瓦瑞知道埃德会这样做的。然而,有一些关于埃德“在那里”的情况(他愿意“包容”瓦瑞的冲动,并且不会被瓦瑞的冲动所折磨),这一点也使得瓦瑞有可能控制冲动。因此,我们的病人带给我们的是他们无法包容的东西。当它不能损害我们的时候,他们也就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作为“抱持者”的意义体系
在成人生命中,抱持构成了成人体验的基石;它是生命得以建立的基石。除了那些感觉无法独立运作的人,它很少在关系基调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大多数人来说,抱持被抽象化进入了一个意义体系,同时成为一个容器,使其他所有关系变得有意义。因此,对婚姻制度的信任使得一份婚姻关系度过了吵闹和令人不满意的时期。宗教信仰使人们有可能忍受痛苦。我们被更大的意义体系所抱持(通常是去个人化的),这些意义体系通过提出一些“要坚守”的信念来锚定我们的生活并使我们感到安宁。
第二部分 第3章 抱持(5)
对一些人来说,赋予意义的抱持功能存在于一些特定的人身上,而不是存在于制度或抽象的理想之上。在试图理解极度悲痛的过程中,马瑞斯(Marris,1982)提出,对一些人来说,失去挚爱之人无异于失去存活于世的所有意义和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挚爱之人的功能不仅是作为依恋对象,还作为运载器,运载那些包容并且建构生活的东西。因此,失去抱持之人的体验仿佛是毫无目的、毫无地点地在宇宙中坠落。(然而,并无证据证明,被制度或观点所抱持在价值、健康或成熟方面或多或少要胜于被人所抱持。理想化的事物和人是一样脆弱的。)
他人的这种赋予意义的抱持功能通常只在个体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或遭遇严重破坏的时候才变得清晰起来。例如,在大屠杀中,人类世界中所有的理性和可预测性都停止了,人们就不得不寻找被抱持的方式。
雷切尔
20世纪40年代早期,雷切尔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村庄中。3岁的时候,她目睹了父母被谋杀的过程。那个时候她并不明白她的父母是犹太抵抗运动的斗士,但是她记得人们的谈论,谈论收留她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但是,她母亲原来的一个女仆(南妮)来到她这里把她带回家中。一年后,这个女仆和她的家人也被杀了。
“南妮、她的丈夫和我都在外面野餐。我们听到了盖世太保的声音,他们让我躲在毯子的下面,我记得我非常害怕。盖世太保踏上毯子,把他们带回屋子里。我记得我听到了很大的声音,但我还是待在毯子下面。过了很长时间,我走进屋子里。屋子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墙壁上也空空如也。我记得我看到他们仰卧在地板上,我感到很害怕。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感到的最强烈的感觉。
早上,她姐姐来了,在灌木丛中发现了我。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告诉我这些人不是好人,是对抗耶稣的。她说她会把我当成她的孩子来抚养,她给了我一个十字架带着,并从未让我走出这个院子。
虽然有这些混乱,我还是感到有人非常关心我、为我担忧。我记得那种被抱持的感觉。人们不怕麻烦地来照顾我,使我继续存活。我知道在我的身边发生着很多牺牲。我多次听说我的母亲请求南妮把我带走并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我的母亲担心她不能躲过战争之劫。我并不能确切记得我的母亲,但是我记得她的头发,我还记得那种被抱持的感觉。在那段时间里,尽管所有人都变了,我却一直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
当雷切尔5岁的时候,纳粹发现了她并把她关进了集中营。她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只是因为她要被用在一次医学实验中。在集中营中,一个失去自己孩子的妇女依恋上雷切尔,这个妇女尽她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做雷切尔的安慰者。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直到这个妇女也被杀害了。
战后,雷切尔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在她的体验中,这对夫妇是冷酷并且无爱心的。这对夫妇的婚姻是麻烦频出并且充满暴力的,他们希望她这个收养的可爱女儿能够成为他们之间的调解者。在回顾过程中,雷切尔现在能够明白养父在某种程度上期望她这个“孤儿”能够成为秀兰-邓波儿。而雷切尔看上去显得瘦小、体弱、头发稀少,而且非常恐惧饥饿,因此无法学会餐桌礼仪。她从最开始就感到养父对她有很深的排斥感。然而,她的养父母确实在经济方面给她提供了帮助,并且使她有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很短的时间里,雷切尔学会了在她的新世界中,要“达到目标”所需要的东西。她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被人喜欢,因此她着手系统地打造自己,使自己变得可爱。她成为一流学生并且很受欢迎,但她从未谈及过去的生活。她将自己经历中更为“真实”的部分埋藏在内心,这一点使她无法与任何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一旦我学会按照伦敦中上阶层的规则来游戏的时候,我就证明自己是个做梦的小孩。我从未谈及大屠杀,也从未谈及我的内心世界。我将他们愚弄的团团转,按照他们的规则游戏人生,从中我得到了一些堕落的快感。”
当她17岁的时候,雷切尔离开了她的养父母,搬到以色列。在那个理解大屠杀并为犹太人而建造的故土上,她找到了她感觉能够建立真实生活的人和社会价值。与那个将要成为她丈夫的以色列男人在一起,雷切尔第一次感到足够踏实,能够开放她自己,与他人建立真实可信的联系。她感到了足够的“抱持”,能够结婚,有小孩和朋友,拥有一份助人的职业,并努力用尽其他每个人都努力用的方法来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
第二部分 第3章 抱持(6)
雷切尔的痛苦经历通过很多方式得以显示,但有关抱持的体验是尤为有启示
华人心语心理咨询热线电话和心理治疗电话:02784530206
国家注册高级心理咨询师QQ362890071 MSN:www.hrxl.cn@qq.com skype帐户:www.hrxl.cn
新浪UC号码217271074【面询请电话或QQ提前预约时间】电话心理辅导时间:中国大陆北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3:00—18:00、晚上19:00—22:00
MSN:www.hrxl.cn@qq.com skype帐户:www.hrxl.cn
新浪UC号码217271074【面询请电话或QQ提前预约时间】电话心理辅导时间:中国大陆北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3:00—18:00、晚上19:00—22:00
症状是心灵的语言——心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各类心理障碍电话心理辅导及心理疾病的网络心理咨询
网上心理医生心理治疗在线联系方式QQ362890071
 MSN:www.hrxl.cn@qq.com skype帐户:www.hrxl.cn
新浪UC号码217271074【面询请电话或QQ提前预约时间】电话心理辅导时间:中国大陆北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3:00—18:00、晚上19:00—22:00
心理咨询电话:02784530206
MSN:www.hrxl.cn@qq.com skype帐户:www.hrxl.cn
新浪UC号码217271074【面询请电话或QQ提前预约时间】电话心理辅导时间:中国大陆北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3:00—18:00、晚上19:00—22:00
心理咨询电话:02784530206
- 热点社交恐惧症
-
 经常骂人说人坏话对自己...
经常骂人说人坏话对自己...
- 推荐社交恐惧症
- 相关社交恐惧症
-
 经历社交恐惧症的困惑与...
经历社交恐惧症的困惑与...
-
 童年经历对学校异性交往...
童年经历对学校异性交往...